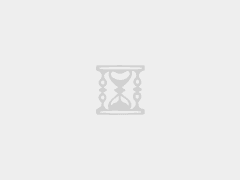摘要:方勇先生提出的“新子学”理论不仅为先秦诸子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视角,而且对于其它学术门类也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新子学”提炼出子学精神这一概念,其核心要义是争鸣对话、多元共生、独立自由。以“子学精神”为视角重新审视经学,可以发现经学虽然推崇权威和一元,但也不乏子学精神。首先,经学本身具有多元性,因为任何解经者都不可能获得经书全部的微言大义,因此需要广存众说。其次,经学“出身”于子学,构建天人、君民、社会、身心等秩序是其共同的主题和目标。第三,解经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可以自主运用多种子学思想资源诠解经书。经学所具有子学精神,及其与子学的互通与互动,使经学的“经性”被削弱和动摇,拟经、疑经、改经即其表现。正是这些子学特征所带来的生机与活力,才推动了经学不断向前发展,使经学具有了应对解决不同时代问题的视野和能力。关键词:经学;子学;“新子学”;经子关系
近年来,方勇先生提出的“新子学”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新子学”以多元性和主体性为学理支撑,试图从整体上对先秦诸子的思想内涵和价值以及在现代性语境下的作用进行观照。“新子学”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为先秦诸子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视角,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其它门类也有重要参照意义。“新子学”不但关注作为具体学术门类的子学,而且还升华出子学现象和子学精神这类抽象概念,对此方勇先生有明确阐述:
所谓“子学现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
据此可知,多元共生、独立自由、争鸣对话是子学精神的核心要义。从表面看,子学精神与崇尚一元性和权威性的经学好像格格不入。然而,如果重新审视经学的全部发展历程,就会发现经学其实也具有鲜明的子学精神,而正是这种子学精神,才推动了经学的不断发展。本文即以此为视角,深入探讨经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子学精神,以展示传统经学的另一种面向。为避免歧义,本文所称的经学,指的是汉代之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诠释六经及其相关传记为目的的学问;子学不但指先秦诸子,还包括秦汉之后基于子学精神独立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学术体系,如佛教、理学等。
一、固有的多元性:经学内部的分派与争鸣
从某种角度看,学术的本质就是多元与争鸣。任何一种学术,如果只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学说,让后人世代遵守,那它本身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甚至不成其为学术。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分为三,佛陀之后有大乘、小乘、空宗、有宗等诸多分派,即其明证。经学虽然崇尚一元和权威,但其内部的多元性及其所导致的分化与争鸣从未间断。
经学兴起于西汉,最初是从民间发展而来,由于各自师承不同,有很多不同的学派,如《易》有施、孟、梁丘、京、费氏等,《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齐、鲁、韩、毛四家,《礼》有庆氏、大小戴氏,《春秋》有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五家之传。不仅一经分为数家,而且各家内部也进一步分门别派,如公羊学在汉代就分化为颜氏、严氏二家,《左传》在魏晋时期有杜氏、服氏等等。各家学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经书进行阐释,并且还经常进行激烈的讨论和争鸣,使严肃、枯燥的经学展现出活泼、活跃、开放的气象。例如,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曾作《春秋左氏膏肓》《春秋谷梁废疾》《春秋公羊墨守》等,从公羊学的立场上对左氏、谷梁进行批评,而郑玄则针锋相对,作《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对何休的观点进行一一反驳。
分派不但是经学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也为官方所允许和承认。从汉至南北朝,官方对经学内部的分派与争鸣采取了充分包容的政策,每一经并不只确立一个权威解释,而是尽量容纳各家异说。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各家学说尚未完全分化,到汉宣帝时,异说纷纷出现,各家都迫切希望得到官方的承认,于是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在石渠阁举行会议,讨论各家异同,“上亲称制临决焉”。经过讨论,确定十二家学说为官学,即所谓的“黄龙十二博士”。到东汉初,各家学说又有兴废,并正式确立了十四家官学博士,终汉世未变。没能立于学官的其它各家,例如《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等,因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民间传习者甚众,官方也采取多种方式予以支持,如另选学生专门学习这些学说等。东汉建初八年(83),汉章帝下诏:“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汉安帝延光二年(123),“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西晋时,多学说并列学官的做法被承袭,官方设立的经学博士比东汉更多,达到十九名,《宋书·礼志》载东晋初荀崧上书云:“世祖武皇帝……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据学者考证,这十九家博士分别是:《周易》郑玄注、《周易》王肃注,《尚书》郑玄注、《尚书》王肃注,《毛诗》郑玄注、《毛诗》王肃注,《仪礼》马融注、《仪礼》郑玄注、《仪礼》王肃注,《周礼》马融注、《周礼》郑玄注、《周礼》王肃注,《左传》贾逵注、《左传》服虔注、《左传》王肃注、《左传》杜预注,《公羊传》颜安乐注、《公羊传》何休注,《谷梁传》尹更始注。可见当时经学异说之广。东晋南朝,博士员有所减省,一经一博士渐渐成为新的主流,但一般仍有九到十名博士。
唐代以降,官方对经学的控制有所加强,一种经书官方只承认一种解释体系,唐初颁布《五经正义》,为每种经书各编撰了一部权威解释,后又增加为九经正义。宋代曾颁布《三经新义》作为经书的权威解释。元代恢复科举考试,重新确立了每一部经书的权威解释,如四书用朱子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等等。明初编纂了以朱子学说为核心的《四书五经大全》,并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虽然官方致力于经学的统一,但经学内部的争鸣,甚至民间经学对官方经学的质疑与挑战也从未停息,例如明代对官方朱子学说的质疑就非常多,到中晚明时代,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对朱子的质疑和批判甚至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
经学内部的分化与争鸣,还体现在经学学说的不断更新迭代,后人对前人不断否定与超越上。汉代立于学官的主要是今文经学,在民间有古文经学对其挑战与质疑。魏晋时期郑玄经学大兴,又出现了王肃等一批质疑者。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义疏之学,则是对汉魏古注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宋明时代,学者们努力突破旧注疏的束缚,热衷于另创新说,形成以说理为特色的理学化的经学。延及清代,经学之风又为之一变,全面否定了宋明时代那种以意说经的风气,强调朴实考证之学,形成考据经学。经学正是通过这种对前代的不断否定与超越,才得以持续的传承和发展。
经学作为一个崇尚权威的学术体系,何以能够如此容忍多元、争鸣与分派?这与经学自身的理念有密切关系。经学家认为,经书是圣人所作,其中蕴含着圣人的微言大义,但去圣久远,大义难明,每一位解经者受其能力的限制,都不能完全把握这种微言大义,每个人可能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小的方面,即所谓的“一得之见”,解释的人越多,便能够越接近圣人的本意。所以,经学史上一直存在这样一个信念:经书应该广存众说,而不应定于一尊。前引汉章帝诏书所说的“扶微学,广异义”,即是明证。古人常把解经比喻为射箭,经书本义比喻为鹄的,射的箭越多,中的的可能性越大;又常比喻为罗鸟,所设网罗越多,捕到鸟的可能性也越大。明代娄坚曾说:“昔闻通儒之论,以谓圣人之经宜存众多异同之说,以待读者自得。”为解释经书提供自己的一得之见,以图增进对“圣经”的理解,这也是经学中始终存在分派与争鸣的内在原因所在。
二、建构秩序:经学与子学的内在一致性
经学内部存在着固有的多元性,这是经学中子学精神的重要表现。而从内在特质上讲,经学与子学也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相通性。
从源头上看,经学的前身是子学。经学虽然汉代才正式成立,但其创始则要追溯到孔子。孔子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对古代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形成一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学术体系,这种学术体系后来渐渐被凝聚到古代六部典籍即六经中,从而形成经学。孔子只是诸子之一,而经学的前身也只是子学之一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春秋到汉初的‘经学’实际上只是儒门一家之学,为‘子学’一支。”经学在汉代的官学化,也是以子学为其开导先路。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书从其“出身”来看,即不同于西方的经书,西方的经书多是由神创造或言说的,而中国的经书只是一位贤能的诸子汇编整理而成,是“一家之言”。这是经学的“基因”之一,也成为经学与子学内在相通的根本依据。
从问题意识和目标宗旨看,经学和子学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无序的社会现状,而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秩序。经学主张承续先王之道,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秩序。在经学视域中,经书被认为是先王政典,是圣人修齐治平的经验和精华所在,是指导人生、社会和国家最高原则。经学致力于在经书的指导下,建构一个从天到人的和谐秩序,大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天人秩序,即天道论,为人和天地万物安排一个合理的架构,这方面以《周易》为代表。二,君民秩序,即政治理论,建构一个从天子到民众的人间秩序,并确定处理这一秩序的基本原则,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保民爱民、《春秋》的名分、“三礼”的礼乐治国、《诗经》的诗教理论等方面。三、社会秩序,即伦理学和社会学,确定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如五伦等,这一点在诸多经书尤其是《礼记》《孝经》《论语》《孟子》中有系统阐述。四,身心秩序,即修养理论,强调个人的品德修养、志、节等身心关系,以及个人修养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多见于《尚书》《论语》等经书中。再看诸子百家,虽然异说纷纷,但其目标也无非是要改变现实的无序而回归有序,即务于治道。《淮南子·泛论训》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爲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可见,无论是早期经学还是诸子百家,都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而产生,只是提出的方案不同而已。翻开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管子等诸子之书,其要义无有出此四种秩序建构之外者。由此可见,经学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宗旨,与子学是高度一致和重合的。正如刘兵先生所指出的,经学与诸子都致力于建构政教关系,他们的不同只是“在朝和在野的区别罢了”。
每一种经学、每一个时代的经学,无论其形式如何呆板,其内容如何繁琐,其实都在建构上述四个方面的秩序中贡献了智慧,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学。汉代经学,《春秋》学方面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谴告说,《尚书》学的代表成果是《洪范》的五形和灾异论,《诗经》学则有大小序所建构的诗教理论,等等。即使以训诂考据为主要特色的郑玄经学,也不能仅以考据视之,他之注“三礼”,并把三礼建构成一个完整的礼学体系,其中蕴含着重整礼法以恢复社会秩序的理念。宋代《春秋》学复兴,很多学者通过注解《春秋》表达个人观点和理想抱负,尤其是产生了《春秋》第四传——《胡氏春秋传》。《胡氏传》何以会产生?这与宋代政治经济的危机和两宋之际的动乱局面密不可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此书的目的是“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可见其宗旨无非是重新建构家国天下的秩序,这几乎就是经学面具之下的子学。宋代另一只非常兴盛的经学是《周礼》学,这是因为学者们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是治理天下的模板和典范,相关经学成就不但有李觏的《周礼致太平论》,陈傅良、徐元德的《周官制度精华》,唐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郑伯谦的《太平经国之书》等著作,更有王安石以《周礼》为经典依据进行的社会改革。总而言之,经学的内核是建构秩序,从这个角度上看,说经学是披着神圣外衣的子学,可能也不为过。
三、主体意识:经书的子学化诠释
经书作为一个神圣的体系,其内容是凝固的,但经学则是一个活跃的思想学术体系,经学家可以采取不同的角度、立场进行解经,既可以引进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可以用其自创的子学思想进行解经,这体现了解经者在诠释经书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强调以我为主,这与作为诸子的主体意识是高度一致的,从而使经学的子学特征更为明显。
汉代经学高居官学,子学走向衰落。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局势的混乱与春秋战国颇为类似,导致经学走向衰败,而子学则日渐复兴,主要表现在佛道二家的兴盛。道家以玄学的形式重新恢复活力,道教神仙之学也依附于道家而兴起,同时从西域传来的佛教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时期的经学家往往主动引子学解经,使经学的发展表现出些许活力而不至过分暗淡。魏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和《周易注》,开以道家玄学诠释经书的先河,并且多有创见,对后世影响深远。特别是王弼的《周易注》,跳出汉代繁琐的章句之学和象数易学的窠臼,以义理解经,使易学为之一新,在后世成为《周易》的最权威注解。清代学者姚振宗说:“以玄义释经者,自魏王弼《易》始,历晋宋齐梁,是类之书不知凡几。至隋唐之际,五经家犹存此及张讥、沈文阿三家,他如《周易玄品》《周易普玄图》《孝经玄》,大抵亦其类也。”由此可见玄学对经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佛教对经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众多的经学义疏中充斥着大量的佛教名相和义理,张恒寿先生将其分为五类,即佛典名词之引用,佛典论证语句之模仿,佛经疏解方法之采用,佛教教义传说与儒书之牵合,佛教学理与儒家学说之杂糅等,由此可见经学对佛教的吸纳之广泛。很多僧人也将佛教经书与儒家经书等而视之,以佛理解经注经,例如释慧远曾讲《丧服》(《高僧传》卷六)、释慧琳注《论语》(《宋书·颜延之传》)、释灵裕着《孝经义记》(《续高僧传》卷九)等。就连专讲丧礼服制的《丧服经》,也成为佛道学者借以讨论名理的重要资源。
宋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创期,学者们在批判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挖掘先秦儒学思想资源,纷纷创立新说,形成博大精微的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理学家虽然也解经注经,但他们的身份首先是思想家,是诸子,其次才是经学家。最关键的是,他们对经学有着不同于过往的新认识。他们认为,解经、读经要以我为主,重在个人真正有所得,有所体会,于身心家国有所帮助。这种认识使解经者在经书面前不是完全跪倒膜拜,而是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我注六经”,这里的“我”要加着重号,强调是我在注六经,要以我自己的思想、立场乃至体悟去诠解六经。其二,“六经注我”,强调六经是为我的思想理论和身心修养服务的。无论哪个方面,都是解经者主体性的表现。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理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完全贯彻了他的理学思想。例如,对于《论语》“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朱子注云:“天,即理也,其尊无对,非奥竈之可比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直接把“天”解释为“理”。又如释《论语》“吾斯之未能信”云:“斯,指此理而言。”可见,《四书章句集注》既是一部经学著作,更是一部子书,是以子学诠释经学的典型。到了明代,王阳明通过对朱子《大学》格物说的反思,创立了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思想体系。在龙场悟道后,他立即撰写了一部《五经臆说》,目的是“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但其目的不在解经,而是用经书之言来印证自己的思想,是典型的“六经注我”。他虽然没有对四书进行系统注解,但从其对相关章句的论说中也可以看出鲜明的心学色彩,例如对于《论语》“好古敏求”章,他解释说:“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受其影响,晚明出现了大量的以心学为基调的四书诠释书,如季本《四书私存》、罗汝芳《四书答问集》、焦竑《四书讲录》、袁黄《四书删正》、周汝登《四书宗旨》等。这些著作思想活跃、广收博采、富有批判性,往往融儒释道于一炉,具有鲜明的子学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的四书学也被称为“新四书学”,以有别于朱子“格物穷理”色彩的四书学。
主体意识使经与解经者不再是严格的主仆关系,而更接一种平等对话甚至我主经仆的关系,使经学摆脱凝固、腐化、呆板的状态,而重新具有向前发展的活力,和与社会互动的能力。
四、动摇:经书权威的变动与突破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中国经学具有多方面强烈的子学精神,正是这种子学精神,不断动摇经书的权威性和一元性,使中国经学表现为一种弱性经学,用玄华先生的话说,就是“子学返而辅之,不断地用子性去剥离、消解经学文本身上的经性”。这是中国经学区别于西方经学或宗教经学这类强性经学的一个重大不同。“经性”的消解,可以从拟经、经书范围变动、疑经改经等现象中略窥一斑。
首先,由于经学“出身”于子学,孔子以诸子身份可以创经,后世同样有此志向者,亦可以模仿孔子而作经,这就是中国经学史上奇特的拟经现象。据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古今拟经之书达352部,遍及六经四书等各部经书。最早的拟经者是汉代的扬雄,《经义考》把他写的《太玄经》作为第一部拟经。《太玄经》模仿《易经》而作,张衡评价说:“观《太玄经》,知子云殆尽阴阳之数也,非特传记之属,实与五经相拟。”认为此书的价值跟五经相当。除了《太玄经》外,扬雄还拟《论语》而作《法言》。扬雄通过模拟经书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他虽然生活于经学时代,却是汉代子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拟经者是隋代的王通,他尊崇王道,自比孔子,并模仿孔子删述六经,撰写了一套续六经,包括《续书》《续诗》《元经》《易赞》《礼论》《乐论》。关于写作续六经的目的,他说:“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由此可见,王通拟经的背后体现的正是经学最源始的“子学意识”,拟经者不再受原有经书权威的束缚,反而是要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传统,自我作古,自作权威,把自己的胸怀和思想用文字表述出来,并自认为可以作为后世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参照,具有“经”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经典的固定性被认为是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扬·阿斯曼教授所说:“卡农(经典)形成的关键步骤是“关闭大门”(阿拉伯语称之为jǧtihad)。所谓关闭大门就是在卡农与伪经之间、原始文献与注释性文献之间划一条具有决定性界限。被称为卡农的文本不能被补写和改写,这是它与传统流之间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差别。”关闭经典的大门,严格区别经典与非经典,就是使经书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而中国的经书并不如此,其界限非常模糊,其范围变动不居,这与不同时代的子学思潮有密切关系。汉代的经书主要是指《易》《书》《诗》《仪礼》《春秋》五经,外加《孝经》《论语》这类小经,尤其重视《春秋》《孝经》,因为董仲舒等汉代《春秋》学家把《春秋》当成孔子为汉立法之书,而把《孝经》当成体现圣人言行的模范。到魏晋南北朝时,受佛道二教的冲击和影响,经书范围渐趋混乱,《礼记》《周礼》及“《春秋》三传”等皆具有了经的地位,其中三礼学尤为兴盛,道家的老庄甚至与《周易》并称为“三玄”。宋代以后,由于理学的兴起,《大学》《中庸》《孟子》等专讲义理之书渐受青睐,逐步升格为经,其重要性超过原有的六经,甚至成为解释六经的依据,朱子就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到元代重兴科举考试,遂正式形成四书五经的经书体系。明代经学中四书学一家独大,而四书学中,《大学》诠释又是重中之重,阳明心学的成立正与《大学》诠释有密切关系。清代,经书范围又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段玉裁甚至提出将经书扩充为为二十一经,增加《国语》《大戴礼》《史记》《汉书》《说文解字》《九章算术》等,这又是当时考据学推动的结果。总而言之,经书范围的变迁和体系的转换,与子学的推动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疑经改经也是经书权威弱化的重要表现。疑经的历史很长,早在东汉时马融就曾怀疑《尚书》中的《泰誓》篇是伪书,但那只是基于文献学考察的结果。宋代之后,由于思想界的活跃,经书权威受到影响,疑经改经才真正蔚然成风,王应麟引用陆游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清人皮锡瑞说:“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宋人疑经的根据在于把“理”当作最高权威,而经则需要理来衡定,只有符合理的才是真经,否则都是值得怀疑的。陆九渊的一段话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昔人之书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顾于理如何耳。盖书可得而伪为也,理不可得而伪为也。使书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书之所言者事耶,则事未始无其理也。观昔人之书而断于理,则真伪将焉逃哉?苟不明于理而惟书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伪而取之,则其弊将有不可胜者矣。……使书而皆合于理,虽非圣人之经,尽取之可也。况夫圣人之经,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于理,则虽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
“观昔人之书而断于理”,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疑经的理论依据,一切书籍包括圣人之经都要放到理的显微镜下进行检查,才能决定真伪。四库馆臣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范文澜先生也说:“宋人讲理,理就是圣人之性,是绝对的。一切以理为依据,不合乎理,就必须受到批判。朱熹所以对《尚书》提出怀疑,就是它觉得《尚书》不合乎理。朱熹学生王柏删《诗》三十二篇,也是因为那些都是淫奔之诗,不合乎理。”疑经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改经,程颐曾对《周易》《尚书》进行改正,朱熹对《大学》《孝经》也进行过修改。疑经改经发展到王柏达到极致,皮锡瑞指责他说:“若王柏作《书疑》,将《尚书》任意增删;《诗疑》删《郑》《卫》,《风》《雅》《颂》亦任意改易,可谓无忌惮矣。”经学家何以有疑经改经的勇气?无非是他们心中有了一套足以自信的理论体系,才敢怀疑甚至更改神圣的经书。如果没有子学精神的激荡,经学家可能只会将经书视为神明之物,而永远匍匐于其脚下。
结 语
“新子学”的提出,虽然主要针对传统子学尤其是先秦诸子,但其理论意义显然不限于子学,而对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这也是“新子学”始终坚持主体性的原因所在。以“新子学”为视角观照秦汉以来的传统经学,可以发现经学具有非常强烈的子学精神,这可能是中国经学重要特征之一。而正是这些子学特征所带来的生机与活力,才推动了经学不断向前发展,才有了汉人之经学、唐人之经学、宋人之经学,乃至明清和近代以来的经学,使经学具有了应对解决不同时代问题的视野和能力。学界虽然将汉代之后划为经学时代,但子学并非不再存在,只是经学常与子学混在一起,难以区分,经学中有大量的子学因素,而子学也往往是以经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不能把经学绝对化,把经学与子学对立起来,或者如传统观点那样,认为子学只是经学的“支与流裔”,是“小道之可观者”,是“六经外立说者”,毋宁可以这样概括二者的关系:子学是内容,经学是形式。当然,在经学时代,由于经学成为笼罩在子学之上的形式,使子学的开展受到无形的限制,其思想的深度、广度和精彩程度都难与先秦子学媲美。这种对于经学与子学关系的新认识,或许对于研究经学时代子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原载:《诸子学刊》第25辑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微信 美文-微信文章库-我的知识库 » 曹景年: 中国传统经学中的子学精神——以新子学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