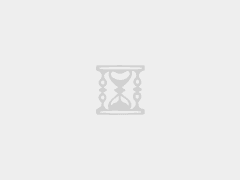“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定评。毫无疑问,《史记》是一部严肃的史书,但它同时具有较高的文学性,是一部以写心见长的文学经典。
那么,《史记》写的是谁的心?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自然是历史人物之心,还有自己之心。有学者甚至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但为中华民族述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写心。人们读《史记》,不仅可以读到历史,还能读到人的命运与人的心灵的历程。
可以说,没有为自己的写心,没有借助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评价,《史记》就不能“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01
《史记》饱含作者对天地敬畏和诘问杂糅之意
由于时代和职业的原因,司马迁不可能完全抛弃天人感应说,但是他却从人物传记的缜密分析中表现出了大胆的怀疑。他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道与人事并不相感应。他在《伯夷列传》中对现实社会这种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不公平世道提出了愤怒的责问: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穅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汉代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之人能“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而正直奋发之人“遇祸灾者,不可胜数”。在现实中,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也不一定会有恶报。因此,司马迁发出了感慨,“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对天道如此激愤、怀疑,不仅仅是因伯夷叔齐之遭遇而生发,更重要的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内心之块垒,其实正是自己的遭遇使然。
在踏入政坛之初,司马迁认为自己应该做个奉公守法、鞠躬尽瘁、竭尽忠诚的臣子楷模,“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可就因为他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遭受腐刑,蒙莫大耻辱。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天道的怀疑,因此就有了《伯夷列传》中的感慨。项羽英雄一世但自负自傲,刚愎自用,不自我省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对此是持严肃批判态度的,司马迁批评项羽之认识“岂不谬哉”!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司马迁也予以深刻地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通过冷峻客观的叙述表达了强烈的讽刺和批评。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屈原列传》中,将自己介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以表明自己的见解。伯夷叔齐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却遭受了如此不公的命运,司马迁对此很有看法。姚苎田评论道:“宕过一笔,不觉畅发胸中之愤。此实借酒杯浇块垒,非传伯夷之本意矣。须分别思之。”表面说伯夷叔齐,实则抒己之怀。屈原传记通过夹叙夹议的写法,既介绍了屈原的基本史实,又赞美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同时借屈原展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悲剧遭遇寄寓了深深的同情。故而李景星喟叹道:“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干脆将这篇传记看成是三个人的传记,李景星的评价恰切而又深刻。这告诉我们在屈原传记里是作者的真实心理和思想感情的流露。
02
《史记》兼含作者对权贵歌颂与揭露之意
皇帝自然是权贵中的权贵,司马迁用多种手法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看法。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司马迁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史官述史的职业要求,要编著一部信史,自然要“不虚美,不隐恶”,尽可能客观“实录”。通过互见法,我们可以清楚,司马迁对刘邦进行了真实全面的再现,既肯定了他能抓住机遇,凝聚团队,坚忍不拔,屡败屡战,最终成功的雄才大略,同时也把他的流氓地痞作风以及滥杀功臣的罪恶行径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对汉文帝这个带有平民情怀的理想皇帝,司马迁则更多的是肯定、赞美和毫不吝啬的歌颂。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其身上的缺点,在《淮南衡山列传》《佞幸列传》等传中对此都有恰到的揭示。汉景帝和汉武帝在他们的本纪中到底如何,我们并不知晓,《三国志》中的一段记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载:
帝(曹叡)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隐切,有隐忍、激切、尖刻义。在曹叡看来,司马迁因直言而遭受宫刑,所以怀恨在心,于是在史书中“非贬孝武”,说刘彻坏话。王肃回答却告诉我们,司马迁为刘启、刘彻父子作本纪在受宫刑之前,所以,事实不是司马“隐切”,“隐切”之人恰恰是当时的皇帝刘彻。“大怒,削而投之”,所以后世读者再也看不到《孝景本纪》《今上本纪》的真正面目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实录并不一定能够做到,但如实为刘彻作本纪应该是不争事实,司马迁通过互见法把这父子俩的真实面目再现出来。通过《封禅书》《平准书》《外戚世家》《酷吏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佞幸列传》等作品,我们看到了他们父子残忍、自私、冷酷、专断的真实一面。对其他权贵的态度同样是赞美与批判并存,这在吕后、曹参、萧何、田蚡、公孙弘、周勃、周亚夫、韩信等人身上都能体现出来。
互见法的使用往往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畏,最高统治者的叙述,对于其阴暗面、黑暗面的揭露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对刘邦、刘启、刘彻等人的处理;二是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一些做出伟大功绩的功勋人物,因为爱所以隐晦之,如廉颇、魏无忌、项羽、韩信、周勃等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有利于文学性的增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表现。这种做法当然也能够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03
《史记》富含自己的感恩与愤懑之意
《太史公自序》非常特殊,绝非一普通序言,我们把这篇作品定性为司马家族的传记,它位于列传之中,是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也是全书一百三十篇的最后一篇,自然应该归于列传之类,当然它还承担了后来的“序”或“后记”的功能。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自叙家世,简介父亲和自己生平,重点写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原因、过程和感受。这里体现出来的首先是自己的感恩、歌颂之情: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如果在《史记》中写心的话,这篇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但在我们仔细研读这篇作品之后就会发现,真正的写心主要体现在这一段,“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当然,真正做到痛快淋漓写心的作品应该是《报任安书》,但此篇非《史记》篇目,与本文主题不符,因此不作讨论。司马迁未遭遇李陵事件之前属于常态人生,在常态下司马迁跟很多人一样,欲为“循吏”,想做忠臣孝子。司马迁忙于工作,无暇交游,可能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可能的是因为得罪的是当朝皇帝,所以在灾难来临时无人敢出手相救,最后只能接受残忍耻辱的宫刑“苟活”于世。
在许多传记的“太史公曰”部分,司马迁从幕后走向台前,往往能够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司马迁在为晏子作传时抒发的是对政治家的赞美,这正表现出对以晏子为代表的政治家识人、得人、重用人的美好素质的肯定。司马迁的为自己写心,当然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他人传记来曲折委婉地表达。《屈原贾生列传》表达的是对于屈原苏世独立、独立不迁、始终不改其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伟大思想和人格的由衷赞美。这与其说是赞美悲剧人物屈原、贾谊,毋宁说是借屈原、贾谊为自己正名定分。《魏公子列传》赞美礼贤下士如魏公子信陵君一样的理想政治家,对其悲剧命运感同身受。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作者寄寓了更多的身世之感。
对传记人物理解深刻,与之相适应,作者之心表现得也更普遍,情感也更感人。又如,《伍子胥列传》“太史公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在此将自己对历史人事的评价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从正面充分肯定了伍子胥的选择,唯其如此才可能“弃小义,雪大耻”,报杀父之仇,成就了一世英名;自己选择了耻辱的宫刑刑罚,与伍子胥一样也是为了扬名后世,光宗耀祖。再看,《绛侯周勃世家》“太史公曰”对绛侯周勃从才能中庸的平民做到身居将相之位,后来吕氏家族谋反作乱,周勃抓住机会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司马迁认为即使伊尹、周公这样的贤人,也无法超过。对周亚夫的用兵,司马迁的评价也非常高,他认为即使司马穰苴那样的名将也难以超过。但是二人最终以穷途困窘而告终,真令人悲伤啊!司马迁肯定了周勃、周亚夫的历史功绩,同时对于他们的悲剧结局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
陈平绝对称得上是汉初政坛上的不倒翁,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的记载相对比较客观,但我们还是能读出作者的心意。姚苎田在将陈平本传与《淮阴侯列传》等传作了比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淮阴侯传》先载漂母及市中年少等琐事,后一一应之。此传亦先载伯兄之贤,张负之识,以后无一笔照顾,而独以阴祸绝世为一传之结。夫阴祸固与长厚背驰者也。削此存彼,史公之于平也岂不严哉!凡此须于文字处会之。
的确,史公书法非常注重前后照应,商鞅、吴起、李斯、韩信、周亚夫等人传记都能做到前后照应,在陈平传记中却“无一笔照顾”,说明陈平之为人“以阴祸绝世”,史公对这个人的评价自然不高,通过在韩信、周勃等人的传记中寄寓的赞美和同情,表达出的是对陈平为人的不屑态度,隐含了深深的批评之意。在司马迁看来,人要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人要信实,说话算话,人要厚道,重情重义,但这些与精于谋划算计的陈平、刘邦等人是扯不上关系的。在《曹相国世家》中,姚苎田认为曹参是“因信之力而参独擅其名”,在“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后,姚氏点评道:“非薄参也,正痛惜淮阴耳。”在“太史公曰”的总评中说:“此《赞》言简而意甚长,不满平阳意最为显著。”
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临终遗命,为了立身扬名,隐忍苟活而发愤著书。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发愤”突显出《史记》一书的个人色彩,增强了其文学性。《史记》之写心,主要是为历史人物这些“他者”写心,形成与历史人物的一场场对话交心,同时这些“他者”身上,作者又几乎无不寄寓自己的心意。今天我们阅读《史记》,也仿佛在与司马迁这位古老的史学家对话交心,随时会聆听到回荡在文本天地里的作者心声。
推荐阅读
中国文学研究
第三十二辑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定价:45 元
ISBN:978-7-309-14489-5
目录
论《诗经》中的“郊” 侯文学
清华简《子仪》辞令研究 何家兴
论《史记》由“他”而“我”的写心之道 张学成
汉赋中的秦史书写——读司马相如《哀二世赋》 蒋晓光
敦煌残卷《楚辞音》所代表的时代与楚辞音义文献的产生 牟歆
写本·刻本·拓本——唐代墓志的生发、篆刻与流传 孟国栋
空间、身份与关系:唐代小说中的盒子 杨为刚
明初君臣唱和与台阁体余来明 周思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金瓶梅词话》的版本形态及其文献价值——兼与梅节本和人文本比较 杨彬
清代孙濩孙对赋的三位一体功能认知与赋史建构 何易展
胡濬源《离骚》“求确”探赜 周建忠 徐瑛子
晚清幕府中的域外诗歌创作——以吴长庆幕府为中心 侯冬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发展 彭松
意随世变——韩愈诗试论 [日]川合康三 著 陆颖瑶 译
最近十年日本的中国唐代小说研究状况 [日]赤井益久 著 陆颖瑶 译
从“文苑”之文到“淑世”之文——《新唐书》列传对“文”的重新定义 [美]田安
END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图书编辑 | 杜怡顺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微信 美文-微信文章库-我的知识库 » 司马迁写《史记》,写的是谁的心?